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老师治学以“勤奋”为先。举一例就可窥见。生活中,我们对日本流行的“暴走族”一词应该不陌生,“暴走”原意是爆发式的奔跑,是日本社会对骑摩托车青少年的称呼,王老师也称自己是“暴走族”,但他的“暴走”是每天通勤一个多小时全靠走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海外访学的中国学者生活普遍不富裕,有的甚至是相当“困苦”,王老师每天坚持“暴走”,是为了省下一笔交通费用,用来支付高昂的文献复印费,他想将珍贵的古籍资料尽可能多复印一些带回国内进行学术研究。如此,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才能做到“绝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而王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些珍贵资料,对改革开放后比较文学领域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治学先“自树”。王老师凭靠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识素养,一方面能够对中国问题做到“知己”,深入体察日本文学及其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能够对日本问题做到“知彼”,从而避免了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尊重。这样的治学态度对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古籍整理及文学史研究不无裨益,还有助于拓宽思维空间,树立开放的研究心态,推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治学更要“树人”。作为国内中日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王老师研究视野开阔,有责任有担当。在常年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中,王老师意识到学术需要传承,对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界来说,中国学者的惊鸿一瞥远远不够,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双方能平等地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在大家都以为学术成绩斐然的王老师,会一直留在日本的时候,他却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返回国内。秉承“勤奋严谨,自树树人”的校训,王老师至今仍坚守在天津师范大学这片教书育人的热土上,先后培养了博士生15人、硕士生20余人。王老师对学生们的要求是:日语的“听”“说”“读”“写”和汉语的“听”“说”“读”“写”这八门功课须样样精通,才能对两国学界“知己、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是深知熟稔,进而做到与日本学者对话无障碍。严师出高徒,王老师的学生毕业后大都活跃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第一线,很多博士毕业生也早已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成为国内日本学研究界的新兴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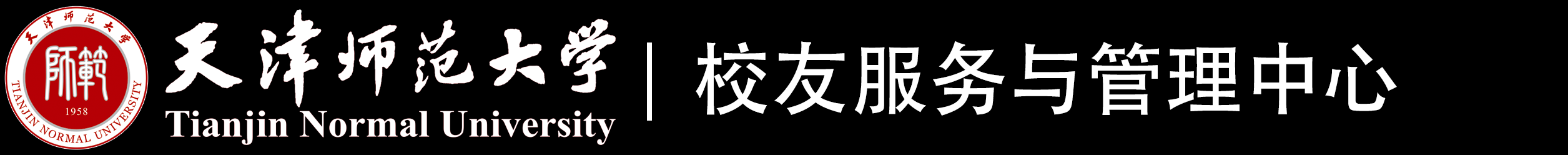 目的地搜索
目的地搜索
